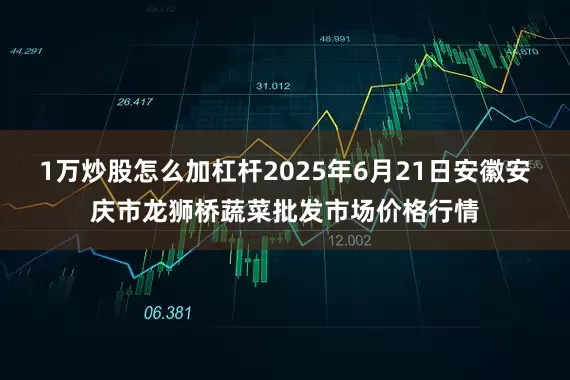如同每一“门”的常规结构,东垣首先一上来就是援引了《内经》的相关内容,来作为整章的理论依据。尽管,最早提出“五积”二字的,应该是其后的《难经》。
但要说到关于“积”的中医理论,过去两千年来还没有任何人能超越《内经》。
【东垣引用《内经》】
积,或是“积”的相似词汇,在《内经》里所涉及的内容,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。而李东垣主要援引的是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篇中的一段文字:
“黄帝曰:积之始生,至其已成奈何?岐伯曰:积之始生,得寒乃生,厥乃成积也。黄帝曰:其成积奈何?岐伯曰:厥气生足悗,悗生胫寒,胫寒则血脉凝涩,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,入于肠胃则䐜胀,䐜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,日以成积。卒然多食饮,则脉满,起居不节,用力过度,则络脉伤,阳络伤则血外溢,血外溢则衄血,阴络伤则血内溢,血内溢则后血,肠胃之络伤,则血溢于肠外,肠外有寒,汁沫与血相抟,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。卒然外中于寒,若内伤于忧怒,则气上逆,气上逆则六输不通,温气不行,凝血蕴里而不散,津液涩渗,著而不去,而积皆成矣。”——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
《灵枢》的此篇内容将来有机会应该会专门做“单篇解”,这里就不逐句解读了。需要先着重强调的是其中,古人的三大顶级认知:
一、【厥+逆】致“积”形成
上段文字关于“积”的病因,追溯到最初,都是因于“厥”,如“得寒乃生”,“外中于寒”。但我们要注意到,紧接着“厥”而出现的“逆”,如“厥气生足悗”,“则气上逆”;
二、气上逆则不达于外
“气上逆则六输不通,温气不行”。
记得我当时读到句话的时候,就差整个人没跳起来了~!古人太TM牛逼了~!
用本号以前的表达来说就是,气机升逆则亦难以外达,升降出入要不偏不倚皆在其位;用本号现在的表达来说就是,阴火线不降→卫气线不升;
三、“积”是津液与血的病理混合物
上面有三句,一是“血脉凝涩…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,日以成积”;二是“汁沫与血(血溢)相抟,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”,三是“凝血蕴里而不散,津液涩渗,著而不去,而积皆成”。这三句是同一个意思的三个说法版本,古人要告诉我们的是:
当血从生理变成了病理之瘀血,当津液从生理变成病理之汁沫,两者相聚而不得散,便会逐渐形成“积”。
【东垣引用《难经》】
而后东垣又再援引了“五积”的真正出处《难经》。由于他接下来会分别在五积对应的五个方子的主要功效里,一一抄写上《难经》里的原文,因而在引文中他就基本略过了:
“故《难经》中说,五积各有其名,如肝之积名曰肥气,在左胁下,如覆杯,脐左有动气,按之牢,若痛者是也,无者非也。余积皆然。”——《东垣试效方·五积门》
【五积门的治疗总则】
在引文的最后,东垣提出了治疗“五积”的总法则:
“治之当察其所痛,以知其应,有余不足,可补则补,可泻则泻,无逆天时,详脏腑之高下,如寒者热之,结者散之,客者除之,留者行之,坚者削之,消之、按之、摩之,咸以软之,苦以泻之,全其气药补之,随其所利而行之,节饮食,慎起居,和其中外,可使毕已。不然遽以大毒之剂攻之,积不能除,反伤正气,终难治也。医者不可不慎。”——《东垣试效方·五积门》
对于上段我这里提炼出重要的两点:
一、遵循《内经》的“补泻”大法则,补则补卫气线(即气-阳-津-血-),泻则泻阴火线(即气+阳+津+血+)。
东垣在其“腰痛门”里,对于诊疗原则曾写过一句话,我认为同样适用于这里,就把它给搬过来了:
“通其经络,破其血络中败血。”——《东垣试效方·腰痛门》
二、谨守顾护正气
药物方面,须两线兼顾;药物以外,亦须注意饮食起居,共同配合。而不可一味攻邪,徒伤正气,反而难以治愈。东垣再三提醒,医者务必谨慎于此。
【关于“五积”】
《难经》里所总结的“五积”分别对应“肝心脾肺肾”,但我们须再进一步,用《内经》的理论来进行统一。
对于“肝之积”(名曰肥气),将其直接理解为是,肝经经脉为主之经气通行不利,发生了【厥+逆】,并在该经脉所过的某处,逐渐形成了“积”;
对于“心之积”(名曰伏梁),将其直接理解为是,心经经脉为主之经气通行不利,发生了【厥+逆】,并在该经脉所过的某处,逐渐形成了“积”;
对于“脾之积”(名曰痞气),将其直接理解为是,脾经经脉为主之经气通行不利,发生了【厥+逆】,并在该经脉所过的某处,逐渐形成了“积”;
对于“肺之积”(名曰息贲),将其直接理解为是,肺经经脉为主之经气通行不利,发生了【厥+逆】,并在该经脉所过的某处,逐渐形成了“积”;
对于“肾之积”(名曰贲豚),将其直接理解为是,肾经经脉为主之经气通行不利,发生了【厥+逆】,并在该经脉所过的某处,逐渐形成了“积”;
之所以加上“为主”,是因为有可能涉及到其它被其波及到的经脉,比如表里经、同名经、主相同功能之经等等。
【东垣之前的“五积”方】
以《难经》的影响力之大之广,“五积”有关的方子想必不可能少。
比如南宋大医家陈无择在其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书里,就专门有个“五积证治”篇,其中的五个方子也都是按照《难经》里的名字来命名的。
我们更为熟悉的许叔微许学士,在其《普济本事方》里则记录过“肺之积”“息贲”所对应的两个方子。
【张元素的“五积”方】
张元素以前的医家们所用的“五积”方,与东垣的“五积门”方差异都比较大。
而东垣的“五积门”方,主要是受其老师张元素的影响。
张元素主张使用《和剂局方》的“温白丸”来通治“五积”:
“肝之积伏梁,温白丸加柴胡、川芎治之。心之积肥气,温白丸加菖蒲、黄连、桃仁治之。脾之积痞气,温白丸加吴茱萸、干姜治之。肺之积息奔,温白丸加人参、紫菀治之。肾之积奔豚,温白丸加丁香、茯苓、远志治之。”——楼英·《医学纲目》
“易老治五积,肺息贲:人参、紫菀;心伏梁:菖蒲、黄连、桃仁;脾痞气:温白丸加吴茱萸、干姜;肝肥气:柴胡、川芎;肾奔豚:丁香、茯苓、远志。”——王好古·《医垒元戎》
【《局方》“温白丸”】
《局方》“温白丸”的药味组成为:(具体的炮制法与剂量,这里省去,可参附录)
川乌、柴胡、桔梗、吴茱萸、菖蒲、紫菀、黄连、干姜、肉桂、茯苓、蜀椒、人参、厚朴、皂荚、巴豆。上为细末,入巴豆匀,炼蜜为丸,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三丸,生姜汤下,食后或临卧服,渐加至五、七丸。
上面张元素所说的加味,大多是“温白丸”本来就有的,我们可以解读为:治“肝之积”倍加柴胡另加川芎;治“心之积”倍加菖蒲黄连另加桃仁;治“脾之积”倍加吴茱萸干姜;治“肺之积”倍加人参紫菀;治“肾之积”倍加茯苓另加丁香远志。
也就是说,张元素只在“温白丸”的基础上,有过“川芎、桃仁、丁香、远志”这四味药的加味,但并未曾减去过其中的任何药味。
【王好古的“五积”方】
作为李东垣亦师弟亦弟子的王好古,他也有自己的“五积方”。
王好古许是看到老师张元素既然始终只用一个方子通治“五积”,他索性就彻底放弃了如陈无择那样治一个积用一个方,而是在“温白丸”的基础上拟了两个通治方,分别为:万病紫菀丸,与,万病感应丸。
从取名就可以看出,王好古想以一丸通治各大经脉之积。
万病紫菀丸,在《局方》“温白丸”的基础上再加羌活、独活、防风;万病感应丸,在《局方》“温白丸”的基础上再加羌活、三棱、甘遂、杏仁、防风、威灵仙,并减蜀椒。
【李东垣的“五积”方】
好了,东垣终于要登场了,我们首先要能从他的方子里,看到他与前人的链接,同时,也要能看到他自己超越于前人的诸多地方。
【“肝之积”肥气丸】
“治积在左胁下,如覆杯,有头足,久不愈,令人发咳逆痃疟,连岁不已。”
药味组成:(具体的炮制法与剂量,这里省去,可参附录)
厚朴、黄连、柴胡、椒、巴豆霜、川乌头、干姜、皂角、白茯苓、莪术、人参、炙噶甘草、昆布、(若治风痫,再加人参、茯神、菖蒲)。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桔梗、吴茱萸、紫菀
→多了:莪术、炙甘草、昆布、(茯神)
【“心之积”伏梁丸】
“起脐上,大如臂,上至心下,久不愈,令人烦心。”
药味组成:(具体的炮制法与剂量,这里省去,可参附录)
黄连、厚朴、人参、黄芩、桂、干姜、巴豆霜、川乌头、红豆、菖蒲、茯神、丹参。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柴胡、桔梗、吴茱萸、紫菀、椒、茯苓、皂角
→多了:黄芩、红豆、茯神、丹参
【“脾之积”痞气丸】
“在胃脘,覆大如盘,久不愈,令人四肢不收,发黄疸,饮食不为饥肤。”
药味组成:(具体的炮制法与剂量,这里省去,可参附录)
厚朴、黄连、吴茱萸、黄芩、白茯苓、泽泻、川乌头、人参、茵陈、巴豆霜、干姜、白术、缩砂仁、桂、川椒、(若黄疸并积大,再加巴豆霜、附子、砒石)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柴胡、桔梗、菖蒲、紫菀、皂角
→多了:黄芩、泽泻、茵陈、白术、缩砂仁、(附子、砒石)
【“肺之积”息贲丸】
“治右胁下覆大如杯,久不已,令人洒淅寒热,喘咳发肺壅。”
药味组成:(具体的炮制法与剂量,这里省去,可参附录)
厚朴、黄连、干姜、桂、巴豆霜、白茯苓、川乌头、人参、川椒、桔梗、紫苑、白豆蔻、陈皮、青皮、京三棱、天门冬。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柴胡、吴茱萸、菖蒲、皂角
→多了:白豆蔻、陈皮、青皮、京三棱、天门冬
【“肺之积”加减息贲丸】
在以上息贲丸的基础上,再加一味红花。
【“肾之积”奔豚丸】
“发于小腹,上至心下,若豚状,或下或上无时,久不已,令人喘逆,骨痿少气,又治男子内结七疝,女人瘕聚带下。”
药味组成:(具体的炮制法与剂量,这里省去,可参附录)
厚朴、黄连、白茯苓、川乌头、泽泻、苦楝、玄胡、全蝎、附子、巴豆霜、菖蒲、独活、丁香、肉桂、(牡蛎)。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柴胡、桔梗、吴茱萸、紫菀、椒
→多了:泽泻、苦楝、玄胡、全蝎、附子、独活、丁香、(牡蛎)
【东垣五积方的特点】
我们先将基于“温白丸”的“加减”药味内容,都集中再列如下:
【肝之积】肥气丸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桔梗、吴茱萸、紫菀
→多了:莪术、炙甘草、昆布、(茯神)
【心之积】伏梁丸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柴胡、桔梗、吴茱萸、紫菀、椒、茯苓、皂角
→多了:黄芩、红豆、茯神、丹参
【脾之积】伏梁丸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柴胡、桔梗、菖蒲、紫菀、皂角
→多了:黄芩、泽泻、茵陈、白术、缩砂仁、(附子、砒石)
【肺之积】息贲丸(加减息贲丸)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柴胡、吴茱萸、菖蒲、皂角
→多了:白豆蔻、陈皮、青皮、京三棱、天门冬、(红花)
【肾之积】奔豚丸
与“温白丸”相比:
→少了:柴胡、桔梗、吴茱萸、紫菀、椒
→多了:泽泻、苦楝、玄胡、全蝎、附子、独活、丁香、(牡蛎)
首先非常明显的就是,东垣主要去掉了“温白丸”里,与对应经脉不相符合的引经药,主要加上了与对应经脉相符合的引经药;
其次在力度上更专更强了,比如针对“肝之积”的肥气丸,更加了软坚化结的药味;比如针对“心之积”的伏梁丸,更加了清心利水安神的药味;比如针对“脾之积”的伏梁丸,更加了运脾通阳清热利湿的药味;比如针对“肺之积”的息贲丸,更加了宣降肺气通行上焦滞气的药味;比如针对“肾之积”的奔豚丸,更加了通利下焦的药味。
其实,若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东垣的“五积”方,皆变换自《局方》“温白丸”,并进行如上的比对,基本上是很难发现它们之间能有什么联系的。
因为,东垣加减涉及的药味太多了,即便未到“面目全非”的地步,也已经“do了半张脸”了~~~
【李东垣自拟的痞气丸】
但显然东垣还没有过瘾~~~
他在大改“温白丸”之后,对于他最拿手的“脾胃”所对应的“痞气丸”,索性来了一个彻彻底底全新的自拟方:
【“脾之积”加减痞气丸】
药味组成:(具体的炮制法与剂量,这里省去,可参附录)
酒黄芩、酒黄连、厚朴、半夏、益智、吴茱萸、红花、青皮、当归尾、茯苓、泽泻、炒曲、莪术、昆布、橘皮去白、熟地黄、人参、附子、葛根、炙甘草、巴豆霜。
这里面的黄连厚朴吴茱萸茯苓人参,与其说是保留了“温白丸”原方里的药味,倒不如说,刚好是李东垣自己平时就惯用的药味。
【两版痞气丸的对比】
痞气丸:
厚朴、黄连、吴茱萸、黄芩、白茯苓、泽泻、川乌头、人参、茵陈、巴豆霜、干姜、白术、缩砂仁、桂、川椒、(若黄疸并积大,再加巴豆霜、附子、砒石)
加减痞气丸:
酒黄芩、酒黄连、厚朴、半夏、益智、吴茱萸、红花、青皮、当归尾、茯苓、泽泻、炒曲、莪术、昆布、橘皮去白、熟地黄、人参、附子、葛根、炙甘草、巴豆霜。
就我个人对李东垣的了解来看,第二个方子更“东垣”,更符合他的用药习惯。看样子,即便是古人,也是在跳出了前人的条条框框之后,才能更自由地做他自己哈~~~
另外不知你发现了没有,本篇初起提到了东垣的“腰痛门”,而到了这里“痞气丸”的自由版本,其药味组成竟然高度神似,东垣治体表经络层面瘀滞的疾病,比如他的“痈疽门”方。
但你要说两者的区别,那就是接下来的:
【五积门几乎不用风药】
本篇一开始就建议,与东垣的“消食大法”一起读,是因为:
两个“门”的用药,都几乎不用风药。
关于消食法不用风药,东垣的意思是,专于化解或攻下阴位之邪,同时予以不同程度的扶持元气。倘若过用走表的辛散药,则既不能去邪,又会重伤气血阴阳。杀敌不成,反重伤己。
而到了“五积门”,“涉事”的主经脉,肝心脾肺肾,皆主要位于阴位。东垣针对这些经脉里的积滞,也多不用风药,除了针对“肝之积”用了柴胡,针对“肾之积”用了独活。
于是我们便会发现,相较于张元素完全保留了“温白丸”含柴胡的原方,王好古的加味主要是各种风药,李东垣甚至连他本来最爱用的柴胡,都几乎摒弃掉了,除了保留作为肝经的引经药。
这恐怕是许多后人都没有发现的地方。
那么…
【为什么不用风药呢?】
一路走到这里,对于东垣诸多地方竟全然不用风药,我总结下来,主要有两大出发点:1、总体之气血阴阳已大衰的情况下,不再用散气耗气的风药;2、问题主要发生在阴位之阻碍时,风药既没有能力消积,亦会重伤正气,也多不用。
风药的特性决定了它最拿手的是,极为彪悍地引气到阳位。而阴位之滞相对而言,并不是风药所擅长的,无论是有形之积滞,还是无形之气滞。
所以东垣对于阴位之滞,若是要助力+气+阳,大多会使用本号以前所说的“三焦”层面的“辛开”药,或是可归入“扶正”类的“补气/温阳”药。即便同时会用风药,其药味与剂量都会很少。
但“痈疽门”“腰痛门”则不同,它们俩的问题本身就都在阳位。所以,行经通络的风药,以及最为彪悍的能直接快速抵达体表的酒,就变成主角了。
东垣的细致细腻细心细化,都处处体现在这些细枝末节处,需要我们火眼金睛地给一一揪出来,因为:
这是一位超顶尖的医家,之所以能为超顶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并学习。
【东垣五积方的加减法】
主要是根据天地之气的升降沉浮来进行调整,比如天冷则减寒凉药加辛温药。
另外有几个特殊的,比如在“肾之积”奔豚丸的加味法里,东垣提到了牡蛎,说若是“积势坚大”,则须再加“烧存性牡蛎三钱”。但紧接着笔锋一转,说若是“㿗疝、带下病”则“勿加”。
不了解东垣的读者一般都理解不了,我们现在凡是下焦湿气,疏泄太过,大多想都不想,牡蛎是必用的,但为什么李东垣要告诫我们说不能用呢?!
因为牡蛎,咸寒,敛涩。但你要说是因为“寒”吧,牡蛎怎么也比不过“奔豚丸”里本来就有的川楝子吧;你要说是因为“咸”吧,东垣又用淡盐汤送下。
那只能理解是因为牡蛎偏于敛涩的关系吧,会较为严重地妨碍到升阳。
除非…“淡盐汤送下”并不是东垣的本意,那就同时与牡蛎味咸有关了。东垣化结行滞时,极少用到咸味药。就比如他治元好问的脑疽,说的正是“禁咸”,东垣认为咸味不利于升阳。
另外就是“肝之积”若是波及到了心之经脉而出现了“风痫”,则再加通利心之经脉的药味菖蒲与茯神;若“脾之积”出现了黄疸,并积块较大,则倍加巴豆霜,再另加附子与砒石,加强行经消积的作用。
【东垣五积方的服用法】
一、递增法&大半法
《局方》“温白丸”只说从少加到大,“每服三丸,生姜汤下,食后或临卧服,渐加至五、七丸”,而李东垣则又体现出了他的细致周到之处:
“初服二丸,一日加一丸,二日加二丸,渐渐加至大便微溏,再从两丸加服,周而复始,积减大半勿服。”——《东垣试效方·五积门》
除了从少加到大以外,东垣还提醒要注意排便的情况。若是大便出现了“溏”,则说明药量已经到顶了,就必须从头开始再重新慢慢增加。并且,等到积块消掉过半,就须立即停药,谨守《内经》的“大毒治病,十去其六”的准则。
二、XX汤下
淡醋汤送下“肝之积”肥气丸;淡黄连汤送下“心之积”伏梁丸;淡甘草汤送下“脾之积”痞气丸;淡生姜汤送下“肺之积”息贲丸;淡盐汤送下“肾之积”奔豚丸。
随五脏之性,使用对应的送服汤药。酸对应肝;苦对应心;甘对应脾;辛对应肺;咸对应肾。
三、根据四季调整药味药量
如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里所写的“凡药之所用,皆以气味为主,补泻在味,随时换气”,以及他在《内外伤辨惑论》里所写的“随时用药”,他在“五积门”的服药注意事项里,同样也是强调,必须根据天时之升降沉浮来调整药味药量。
总原则,即他在“消食大法”里提出的:药味之寒热,须对应所伤之寒热。后者即是实际两线格局的权重占比,仍可与之互参。
【摘录许叔微的语录】
在“五积门”的最后,东垣几乎照搬了许叔微在其《普济本事方》里的一段文字:
“大抵治积,或以所恶者攻之,以所喜者诱之,则易愈。如硇砂、水银治肉积;神曲麦 治酒积;水蛭、虻虫治血积;木香、槟榔治气积;牵牛、甘遂治水积;雄黄、腻粉治涎积;礞石、巴豆治食积,各从其类也。若用群队之药,分其势则难取效。许嗣宗所谓譬犹猎不知兔,广络原野,冀一人获之,术亦疏矣。须是认得分明,是何积聚,然后增加用药。不尔,反有所损,嗣宗自谓不着书,在临时变通也。”——《普济本事方》
“许学士云:大抵治积,或以所恶者攻之,以所善者诱之,则易愈。如硇砂、水银治肉积,神曲、麦蘖治酒积,水蛭、虻虫治血积,木香、槟榔治气积,牵牛、甘遂治水积,雄黄、腻粉治涎积,磔石、巴豆治食积,各从其类也。若用群队之药分其势,则难取效。究是认得分明是何积,更兼见何证,然后增加佐使之药,不尔反有所损,要在临时通变也。”——《东垣试效方·五积门》
这段文字出自《普济本事方》一书中的“积聚凝滞五噎膈气”篇。
许叔微上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有三点:①攻诱兼施,很多时候必须先顺其性才能攻其坚;②择药须功能精准对应,善治水的治水,善消食的消食,诸如此类;③须力专,集中力量攻坚,淡其前提条件必然是得须认得准,具体在什么层面什么经脉什么性质等,随后选用针对性的药味,而不能盲目堆砌各种攻邪药。既会因其不专而难攻下邪,又会因药味剂量过多而重伤正气。
仍是与东垣“消食大法“的准则一致:专于邪,少伤正!
首尾呼应了哈~~~!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升富配资-股票杠杆第三方平台-股票配资官方公司-南京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